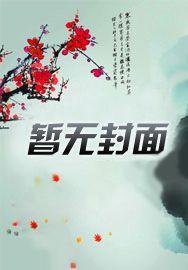飞速中文>昆池劫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他是个符合殿下期望的好皇帝,在位九年励精图治,边境安定,四夷宾服,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等一会儿,」闻禅难以置信地打断他,「什麽叫『在位九年』?」
裴如凇垂下眼帘,长睫半遮住瞳孔,神情无端有些阴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燕王……不,应该叫先帝了。先帝接过的江山是个表面光鲜丶内里全是败絮的巨大包袱,他继位以後,常常批阅奏摺到深夜,遇上紧急军情,无论何时都会立刻处置,天下之事,桩桩件件,都恨不得亲力亲为……」
闻禅:「就没有人劝一下吗?」
「劝过了,可是先帝说自己是行伍出身,体格强健,不怕劳累。」裴如凇搭在桌面的手指微微蜷起,「再说朝政也离不开他,诸子年幼,朝臣各怀心思,地方贪腐成风,边将拥兵自重,他要革除时弊,就得先豁出自己。」
闻禅皱起眉头,但没有打断他,由他继续说下去:「定兴八年六月十五,先帝深夜於通天殿驾崩,事发极其突然,既无遗诏也无口谕,太子尚不足六岁,皇后忌惮朝臣,唯恐他们借题生事,於是先行宣召梁王进宫,托付他主持大局。」
「先……闻琢患的是什麽病,怎麽会突然驾崩?先前一点预兆都没有吗?」
「对外说是过度劳累引发心疾。」裴如凇说,「先帝早有心悸之症,召御医看过几次,脉案药方都能对应得上。」
「实际上呢?」
「先帝因国事操劳,大概常觉精神不济,便召方士入宫为他炼制丹药,靠服食金丹提振精力……」
砰!
桌上的茶具全部蹦了起来,闻禅怒不可遏:「前朝末代那几个皇帝怎麽死的,顺宗怎麽死的,他忘了你也失忆了?陆朔呢?杨廷英呢?满朝文武是都不喘气了吗?为什麽没人拦着他!」
裴如凇像是料到了她的反应,被她吼了也不争辩,像个受气包一样默不作声地低下了头。
「……」
闻禅也知道自己是迁怒,但气得没心情哄他。她辛辛苦苦筹划了十几年,最後甚至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才给闻琢铺出这麽一条通天之路。正因为信任他的能力,才将公主府的势力乃至裴如凇都托付给了闻琢,期待他成为一代中兴之主,希望在她死後那些人能过上太平日子,可是闻琢这个靠不住的竟然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
裴如凇把茶杯向她那边推了推,轻声安慰:「消消气,都过去了。」
刚刚还说着「看开点」「要放下」的持明公主按住了突突跳动的太阳穴,面沉如水,咬牙切齿地说:「继续说梁王和皇后。」
「是太后。」裴如凇很严谨地纠正了她的说法,「梁王掌着豹韬卫,先帝对他还是信任的,太后大概也觉得他是个忠厚的贤王,放心地将辅政大权拱手相让。她想借梁王之势弹压群臣,等梁王翻脸的时候,群臣自然也不会搭理她。」
「梁王辅政两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磨刀霍霍,说不定哪天一高兴,皇帝母子俩的人头就要落地。太后这时候终於坐不住了。
「她这个人眼光很差,偏偏又最喜欢借刀杀人,她以小皇帝的名义传了一封密旨给保宁都督穆温,命他进京勤王清君侧。但是先帝在朝时,已经意识到边郡十都督坐大的隐患,着手限制边将军权,朝廷与边军的关系很紧张。而穆温不但是边将,还是呼克延人,早就跟同罗眉来眼去,与大齐不是一条心了。」
引狼入室是什麽後果,史书上已经写满了教训,可惜人总是在重蹈覆辙。
穆温叛齐,大开国门,引同罗狼骑至兆京城下,梁王战败而死丶太后和小皇帝均被鸠杀。
穆温另立安亲王闻珙的儿子闻修为傀儡皇帝,这其中还有个极为讽刺的巧合,新帝闻修的母亲,正是当年曾与裴如凇定过亲的钟州苏氏之女苏令君。
「然後呢?」
裴如凇摇了摇头。
闻禅难得地露出一丝踌躇之色,顾及着裴如凇的心情,没有直白发问。好在裴如凇善解人意,主动给出了回答:「没什麽好避讳的,我大概是忧思成疾,染了场风寒,就病死了。」
闻禅在心里默算了一下,大约是闻琢病逝後两年,她死後十一年左右,裴如凇也死去了。
可是——
她怀疑地审视着裴如凇坦然的神情,心中暗忖:他真的是「病逝」吗?
裴如凇迎上她的视线,泛起一点含着苦涩和自嘲意味的笑容。
「殿下想问什麽,可以直说。」
在他方才的叙述中,字里行间潜藏着的各种隐晦与不合情理之处,以闻禅的机敏,想必早有察觉。
但察觉是一回事,有没有勇气说出来是另一回事。闻禅苦心筹谋,不惜搭上性命,却只换来那样一个结局,对她而言无异於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