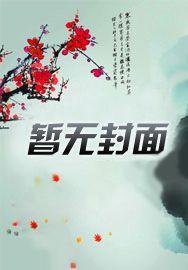飞速中文>假面之罪 > 第一百六十四章(第1页)
第一百六十四章(第1页)
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空气中的泛白浮尘无依无靠地飘着,既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处。
沈藏泽垂下眼帘,目光落在手里的保温瓶上,哑声道:“刑警,本来就是一份无法相信人性,对所有人都抱持怀疑的工作。当上队长后,我才渐渐察觉职业要求跟信念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坚守正义,可面对嫌犯时,我们要设想最坏的情况,要以最恶毒的方式去揣测对方的思想,比起无辜,我们总要先肯定没有人是清白的。”
要坚守正义,就意味着必须保证自己内心的善良,要时刻记得谨守公义的底线。
可当人长时间面对犯罪分子,长时间的凝望深渊,真的能不被影响,不被侵蚀吗?
一旦天平不再平衡,自身的判断又是否真的还能保持公平公正没有任何偏见?
沈义怀疑林霜柏没有错,当年若换做是他不见得就能做得更好,甚至可能会对当年的林霜柏做出更过激的行为,在那之后,沈义也没有逃避自己所导致的结果,而是选择面对和承担。
又喝了一口保温瓶里的菊花茶,沈藏泽用被茶水湿润过后不再那么艰涩的声音继续说道:“所以我不认为你有义务去为他人无法确定的命运以及人生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对你而言,你只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我们做出的判断和行动不可避免的受限于我们的身份,还有经验累积下形成的固定思维以及观念。”
他不会去评价那些与自己无关的普通人,也不会过多去批判媒体舆论,人都是在一个社会里生活的,不管是谁都必然会接受社会化的思想观念灌输,自然也都会受到周围环境以及言论的影响,同时人也是自私并且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机制,在种种前提条件下,用定式思维对不认识不熟悉的人下判断,随身边所有大多数人一起排挤或是疏远某个被贴上特殊标签的人,是很常见的事。
但有些职业是不能犯错的,因为一旦犯错,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人命。
也正因此,在做事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会愈发严苛。
刑警就是其中之一,可刑警也是人,只要是人,做决定时就多多少少会受到个人情绪以及感情的影响,更何况有时候也正是那点直觉和情感会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所以除非是真的带入过多的个人情感又或带有严重偏见的主观看法,否则在他看来只要查案时记住自己的最终目的是查出真相抓住真凶,而不是为了要给某个人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是为了在压力之下必须拿出一个结果去结案,那么无论曾经做出怎样的决定,都能堂堂正正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
“林霜柏的人生无需任何人为他负责,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同样,我也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无法贸然对潘时博现在的生死下定论,但也不排除他已经遇害的可能性。至于他是否杀过人,我认为不是只有亲自结束一条生命才算是杀人,以夺取他人性命为目的而制定详细计划并利用他人执行实现计划,这样的行为,一样是在杀人。”沈藏泽握紧手里的保温瓶,因用力的关系,指节略微发白,他沉着脸,眼底泛起冷光,“他如果遇害,是死有余辜,但我更希望他活着被我们逮捕归案接受法律制裁。”
他不说林霜柏是否已经杀过人,是因为他直到现在依旧相信,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林霜柏不会选择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哪怕是对他做出暴行的第二人格,他也是同样的看法。
第二人格想要的,是让所有人看清真相,让所有人都清清楚楚明白到不管是当年的林顺安还是如今的林霜柏,一直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杀人,恰恰是在印证那些人对杀人犯儿子所抱持的偏见与歧视,所以哪怕是被逼到绝境,第二人格都不会做出杀人这一极端选择。
“我只是想不通,林霜柏为什么会知道许苒被抛尸在那里。”沈藏泽知道,只要无法解释清楚这点,林霜柏的嫌疑只会越来越重。
尽管许苒的尸体上无法找到相关的生物证据去证明林霜柏是杀害她的凶手,可通讯记录证明许苒最后联系的人是林霜柏,而监控录像也拍到许苒最后见的人是林霜柏,再加上尸检报告又具有一定指向性,这些在当前来看都是加重林霜柏嫌疑的间接证据。
如果不是杀害许苒的凶手,为什么会知道许苒的抛尸地点。如果是知道凶手身份,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因为局里有鬼所以就彻底不相信警方了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是早就知道许苒会遇害,却没有阻止而是任由许苒被害,这同样是犯罪。
根据《刑法》规定,监护人、看护人员、警察和医护人员等负有法律上救助义务的人如果明知道会有命案发生却不阻止,将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哪怕是一般人,因不作为而让犯罪分子得逞,依旧会根据实际情况被认定为共犯或帮助犯,必需承担一定刑事责任。
换而言之,即使林霜柏不是杀害许苒的凶手,只要他是故意放任凶手杀害许苒才再尾随凶手去抛尸地点后才匿名报警,他依旧有极大可能性会被认定为是凶手的共犯。
林霜柏跟许苒见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见面时又谈了什么,所有的这一切现在除了林霜柏和凶手以外,没有人知道答案。
从怀里取出几个微型摄像头以及窃听器,沈义说道:“这是在你和林顺安的办公室里拆出来的。”
沈藏泽一愣,骤然抬眼盯着沈义手里的摄像头和窃听器,确认道:“我办公室里也有?”
林霜柏明明只说了自己大学和局里的办公室还有家里安装了摄像头,却并未提及他的办公室也有,甚至还有窃听器。
沈义把摄像头都窃听器都交到沈藏泽手里,道:“算是我当刑警多年的直觉,所以我也检查了你的办公室,你的办公室里没有摄像头但有窃听器;而林顺安的办公室则是摄像头跟窃听器都有,但是分开安装,而且从新旧程度来看,窃听器安装时间远比摄像头要早。”
握紧拳头,沈藏泽只觉太阳穴处的抽痛更加剧烈,他脸颊肉都微微抽搐了一下,咬牙道:“也就是说局里真的混进了老鼠,而且老早就开始对我进行监听,我却居然一无所察。”
连自己办公室什么时候被偷偷安装了窃听器都不知道,他这个刑侦大队长真是丢脸丢到家了,简直就是被人骑到脸上来羞辱嘲讽。
可这也证明了,这只“老鼠”在局里的职位并不低,否则,不可能随意出入刑侦大队长的办公室甚至长时间停留还不引起他人怀疑。
刑侦支队的人就那么多,排除了实习警和成为正式刑警不超过一年的,剩下就都是老人和黄正启、傅姗珊等副队和小分队领队,会是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吗?如果不是,就意味着是其他部门的人,可能进公安系统的都是经过政审等严密背景调查的,还要在局里已经升到跟他相近的位置,会是谁?
如果安善还活着,那么他可能会怀疑到安善身上,因为安善是当年旧案的唯二幸存者之一,并且等级上跟他非常相近,作为跟刑侦合作密切的法医,出入他办公室是很寻常绝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事。
可现在的问题在于,安善也死了。
为什么要杀安善,因为安善发现了什么?还是因为安善是当年的幸存者?
还有安思言的失踪和那篇报道,自从直播自杀爆炸案后,安思言就安分守己了很多,发的几篇报道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进,能尽可能在保证客观性的前提下指出问题,不再像之前那样以极端的攻击性和过度的引导性来吸引流量,让舆论失控。
因此,当那篇针对林霜柏的报道发出后,他其实一直感到有种违和感以及操纵感。
从文笔和遣词造句的习惯上进行分析,那篇报道的确是安思言所写,可现在的安思言有什么理由要在这样刚好的敏感时间去写并发出一篇有明显导向和攻击性的报道?
是对林霜柏进行报复吗?然而安思言并不是那样的人。
安思言这个人虽然年轻冲动,有些想法也比较偏激,做事也有点热血上头不顾后果,可她并不是那种会公报私仇的人,更何况她跟林霜柏之间连有私仇都算不上。
怎么想都想不通的蹊跷之处在新的问题冒出来后,变得更加混乱而让人难以从中理出一条明确的头绪来。
沈藏泽把保温瓶递向沈义,又把掌心的微型摄像头和窃听器都揣兜里,道:“我去重新提审罗英成和闫晋鹏。”
案件卡死就从头开始,只是卢志洲不久前身体情况急剧恶化,不仅发生泌尿系统感染还在几天前进一步确诊肺部感染,因为病情发展迅速,医生表明卢志洲基本已经到了药石罔效的等死阶段;而直播自杀爆炸案的相关人士,潘时博逃逸中,其余知情者已死;因此眼下要想重新进行调查,只能从罗英成开始。
至于安善,人物关系简单暂未发现任何跟案件相关的可疑人士;安思言虽然因为是记者的关系,人际网乍看之下十分复杂,可真要挑出跟本案相关的人,其实也很简单;能汇集到一起的相交点,除了此前的四起案件和刑侦支队,也只有林霜柏。
沈义没有接保温瓶,只是两手插兜里看着自己消瘦许多的儿子,道:“拿走喝完,嘴唇都起皮了。潘时博这个人,假定多年来都没有想过停手,那么他一定一直在关注林顺安,但这里有一个分歧点,潘时博的目的是报复,可另一个身份未明的凶手却未必,从藏尸案开始算起,林顺安回国进入刑侦后才发生的案子,发展到现在能看出,凶手针对的始终是林顺安;合作的人一旦目标不一致,就容易产生冲突,我之所以认为潘时博有一定概率已经遇害,正是基于以上分析。”
潘时博就像是复仇名单的报复者,可另一个凶手却只针对林霜柏一人,到目前为止,林霜柏已经被拉进沼泽难以脱身,可暂时撇开案件受害者和作案手法不谈,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此大费周章,只为了陷害林霜柏,一步步逼迫林霜柏也成为像他父亲林朝一一样的杀人犯吗?可这样做,对凶手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和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