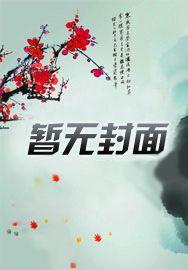飞速中文>君子之剑是哪把剑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不过宁和今日出门,却不是为了买鸡鸭去的。这些日子,她一直在思量,自己以後当做些什麽。
宁和原本自然是与天下有志读书人一样,想要为官,想要施展一身才干,做些实事造福一方。奈何人力有尽而事终不可为。
朝廷封她这个孺人,看似嘉奖,却也从此绝了她的任官之途。乃至於明年京都的会试,想来也是去不成了。
事已至此愁怅无用,只能另辟他径。日後该如何?宁和思索良久,终於下定了主意。
牛车摇摇晃晃,载着宁和朝县城驶去。下了车,宁和就直奔县学而去。
她要去拜访恩师姜教谕。
「你要办书院?」姜教谕一脸惊讶。
他这学生近来声名大噪,整个越州都传遍了。姜教谕走在路上,有时都会遇人恭贺,说他育人有方。旁人以为他该得意,实则姜教谕每回听了,心里头都复杂得很。
当初他做主收下宁和,七分是为践诺,三分也有惜才。後来与这学生相处久了,这三分的惜才就变作了十分。
敏而好学,慧而善思,举一而反三。姜教谕可以毫不吝惜的说,宁和之材,实乃他生平所见之最。更可贵的是,此女不仅才学过人,还兼具品性出众。温而恭谨,谦而内敛,小小年纪不骄不躁,言行已有风骨。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姜教谕看在眼里,叹在心里。如此嘉才,怎是女子,奈何是个女子啊!
朝廷封赏之事传出,外头人人艳羡。唯有姜教谕听了,长叹了一口气。他这学生胸中有抱负,却注定无处施展。姜教谕每每想起都觉遗憾,也曾有心想去信劝慰一番。提起笔来,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今日忽听有学生前来传话说宁和来了,姜教谕讶然之馀,便立刻叫人请她进来。
宁和刚归家时已来拜访过他一回,这次上门,应是另有他事。
宁和说,她要办间书院,就建在滩下村清水河畔。这间书院不论男女,凡有教育之才者皆可为师,凡有向学之心者皆可为徒。村中少小入学皆不取束修分文,外来有家贫者,亦可免去。
不取分文,当何以为继?姜教谕张了张嘴,最终却没有问出口,只道:「你有此志,我当助之。」
有了姜教谕的帮助,当日宁和便在城中找好工人,选址定基丶采买建材,月余之後,一座青墙灰瓦的院落便建成了。
考虑到学生人数与耗费问题,这院子建得并不算大,比起县学更是相差甚远。
前头是片庭院,栽竹种树,设石桌几张,供学子们闲谈休憩所用。中间修有一方木质回廊,廊前是二间宽阔空房以作教室,回廊尽头有两间小室,是宁和准备给夫子们的备课批阅之所。廊後则是东建七八矮屋以作学舍,中修木棚以作食堂,西有水房灶房柴房茅房杂房几间。
一应统共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亩大小。但就这三五亩,也足够把宁和赴考得来的一应赏银给花乾净了。只因她顶要用方瓦丶墙要用砖石,连床铺桌椅也样样不肯马虎,耗费自然也就多。
院落将近完工之际,有会木工的村人抬了空匾过来,宁和提笔写下「岐山书院」四个大字。那村人手脚麻利,第二日便刻好挂上了,又特意请的姜教谕来揭的幕。
岐山脚下,滩下村中,清水河畔,那座後来流芳百世丶享誉千载的岐山书院,就此落成了。
虽然书院是才刚建的,但得益於宁和广为传扬的名气,且还不收束修,很快附近许多村民便都把孩子送了过来。初时只有男娃,後来慢慢也添了些女娃。还是那句话,反正不需费钱,不过是少了些屋前屋後干活的帮手,但放出去学点东西回来,也划算。
至於院中夫子,最初还是靠姜教谕广发书信才替宁和招来了头两个。但到了後来,慢慢的也有了别的读书人愿意前来。第八年时,甚至还来了位女子。
宁和将自己所得赏银尽数投入了建造书院当中,又将其他绢帛之物也拿去卖出,换取银钱供给书院日常开销运营所用。好在有杨氏所留那一屋藏书,只需请人抄录即可,省了许多耗费。加上宁和有朝廷亲封的文昌孺人,虽无实职,却也有俸禄可领。大赵待官吏向来优厚,宁和的正五品封号,每月能领的绢粮银钱皆是不少。
别的五品官员,虽不至於个个骄奢淫逸,也大都青砖大宅丶坐妻拥妾仆婢成群。而宁和却仍旧住在初时的那间村中小院里,青衫布衣,每日往返书院与家中,卯出亥归。一年如此,十年如此,年年如此。
宁和坐在窗边编译着一册注解,凝眉细思,时不时删改几句。而她的左手边,则放着一本摊开的《孟子》,便是她所注之书。宁和着手注《孟子》已是第七年,共分录有十七册,字句斟酌,可谓费尽心力。
她想赶在书院建成第二十年之际,将此书着成,放入山书阁中,也算聊作庆贺。
窗外青竹绿树,虽是清凉,却也招来蝉鸣扰人。宁和坐了一会儿,起身走过去,在窗边站了会儿,将窗扇轻轻合上了。
又是一年盛夏啊。
「先生!」忽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伴随着清脆的笑音从身後传来。
宁和唇边漾起微微笑意,还未回头,先道了句:「慢些,行路当小心。」
只见一杏衫少女头梳双髻丶腰佩粉蓝丝绦,端着方托盘兴冲冲跨进门来:「先生,我给您端了豆糕来!」<="<hr>
哦豁,小夥伴们如果觉得不错,记得收藏网址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span>:||